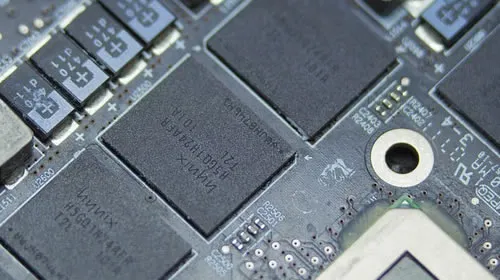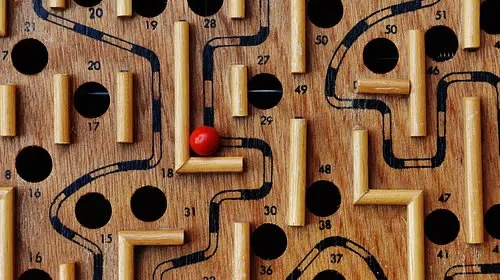秋虫三题
莎鸡
“肃肃莎鸡羽,冽冽寒螿啼”,“寒螀”人们都明白,是蟋蟀,又称为蛐蛐、促织,吾乡称为“土蛰子”。而莎鸡,现代的很多人却不熟悉,尽管在古诗文中经常出现,如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.七月》里,就有“六月莎鸡振羽”的句子,而且在后来的文人诗词中,也有不少写到莎鸡的句子,“谁能事贞素,卧听莎鸡泣”,“任屋角莎鸡促织,吟遍朝昏”等等。
而莎鸡的名字很多,又称筒管娘、络丝娘、纺织郎、络纬、纺花娘等。另一个名字络纬,也是文人们所喜爱的,李白有这样的词句“络纬秋啼金井阑,微霜凄凄簟色寒”,“离家来,络纬鸣中闺”。
而最通俗的名字是纺织娘。
纺织娘显然是文人的宠物,是一种能发声的虫子,而且,很多人把纺织娘和促织当成一种东西了。
纺织娘到底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虫子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也没有搞清楚。弄清楚纺织娘是不是促织,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,确实费了我一些功夫。
《尔雅翼》中的《莎鸡》篇这样写道: 莎鸡,振羽作声。其状头小而羽大,有青、褐两种。率以六月振羽作声,连夜札札不止。其声如纺织之声,故一名梭鸡,一名络纬。今俗人谓之络丝娘,盖其鸣时,又正当络丝之候,故《诗经》云:“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也。”
《尔雅翼》前面的解释很清楚,描述了莎鸡的形象,说明了为什么叫络纬、为什么叫洛丝娘。但是,后面引用《诗经》里的“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也,寒则渐近人。”的句子,却把人引进了误区。
《诗经.七月》里有“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”的句子。在《诗经.七月》的这段话中,说的是两种昆虫,“六月”一句说的是莎鸡,而从“七月”之后,说的是蟋蟀。而《尔雅翼》中,从“六月”到“九月”,说的都是莎鸡了。因而,受其影响,以后的一些文人就把莎鸡和促织搞混淆了,在诗句中也出现了“任屋角莎鸡促织,吟遍朝昏”这样的句子,大诗人李白也没有搞清楚,写出了“离家来几月,络纬鸣中闺”的诗句,莎鸡也跑进屋里去了,从早到晚地鸣叫。
而事实上,莎鸡生活在田野里,不会在屋中鸣叫的,在屋中鸣叫的是蛐蛐,是促织,是蟋蟀。
现在的夏秋季节,在野外还是很容易见到纺织娘的。纺织娘多是浅绿色,身体侧扁,侧面呈纺锤形,翅膀长长的,超过尾部一大截,头部很小,头部的两根须细长,两条后腿也细长。雌性的纺织娘尾部有一根长长的针状物,像雌蝈蝈的尾部一样,不发声。雄性的发声。
纺织娘可以说是身体苗条,很女性化的虫子,这可能是众多名字中带有一个“娘”字的原因吧。
纺织娘多是附在植物的叶茎上,飞起来轻飘飘的,没有声音。发生时,发出轻轻的有节奏的“铃铃铃”的声音,很悦耳。
蝈蝈
蝈蝈,又叫聒聒、蝼蝈、乖仔等,名字众多,因地而异,有的文人们称之为络纬。
蝈蝈肚子硕大,翅膀短短,像马甲一样,覆在背上,两颗大牙露出嘴外。正如贾似道所写,“蝼蝈之形最难相,牙长腿短头尖亮。尾豁过肩三二分,正是雌头拖肚样”。贾似道治国不行,但研究虫子却是很有一套。
蝈蝈长得引人注目,其声音为虫声之冠,更令人喜爱。
夏秋时节,天气晴朗,太阳升起,露水散尽,田野间就响起蝈蝈们的鸣声。声音宏亮,此起彼伏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阵胜过一阵。阳光越强,鸣声越欢。一只只蝈蝈伏在豆棵、地瓜蔓、棘子棵的顶部,震动着翅膀,欢快地弹奏。
小时候,外出拔草,听到蝈蝈声,心就发痒,总想逮几只。听蝈蝈声,就在附近,却不易找到,绿色的蝈蝈,躲在茂密的绿叶间,难以发现。
蝈蝈很机灵,不易逮到。蝈蝈发现有人,就不出声了。如果莽撞过去,蝈蝈就立刻顺着植物的茎杆下到地面,钻进草丛,就难以找到了。只有耐心等待,等蝈蝈再发声。蝈蝈声音再起,就顺着声音,蹑手蹑脚靠近。到了蝈蝈跟前,看清蝈蝈位置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,双手伸出,将蝈蝈罩住。
如果一击不中,蝈蝈就跃到地上,钻进草丛,无影无踪,很长时间不出来了。
别看蝈蝈肚子肥硕,但是,动作灵敏。可不像那些大肚腩的人,动作缓慢。
那时,最喜欢逮的是地瓜叶上的蝈蝈,豆棵上的豆荚、酸枣棵上的刺都有些扎手。尤其是酸枣棵上的刺,很容易把手扎破。
掐两枚大的地瓜叶,把蝈蝈用地瓜叶小心包起,用蔓草缠几道捆住,装进口袋。回家后把蝈蝈放进席蔑编的小笼子,挂到屋檐下或者院子里丝瓜架上。有时笼子用完了,就直接放到丝瓜蔓上、扁豆蔓上。
有月亮的晚上,月光如水,洒在丝瓜、扁豆蔓上,蝈蝈发出阵阵鸣叫。坐在丝瓜架下,看明月高悬,听蝈蝈啼鸣,另有一番情趣。
那时,夏秋时节,村中虫声不断。
不过,儿时逮蝈蝈,并没有明确的意图,只是一种喜欢的游戏罢了。
蝈蝈和人的关系源远流长,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,就有蝈蝈的描述。“喓喓草虫,趯趯阜螽;未见君子,忧心忡忡。 亦既见止,亦既觏止,我心则降。”夏初季节,蝈蝈“喓喓”鸣叫,蚂蚱跳来蹦去。年轻女子,思念心上人,如炙如焚,来到田野。见到了心上人,软语温存,心方安静。
明确记载赏玩蝈蝈是在明代。明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,“有虫,便腹青色,以股跃,以短翼鸣,其声聒聒,夏虫也,络纬是也。昼而曝,斯鸣矣,夕而热,斯鸣矣,秸笼悬之,饵以瓜之饷,以其声名之,曰聒聒儿”。
清代,从康熙、乾隆到末代皇帝他们都对畜养蝈蝈感兴趣,并写诗记载。
那时的富家子弟、有闲有钱之人,也喜欢养蝈蝈。清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·蛞蛞》:“少年子弟好畜秋虫,曰蛞蛞,乃蝼蛞之别种。寄生於稻田禾黍之间,又名曰叫蚂蚱”。
听虫鸣叫,观虫相斗,成了一些人的一种生活乐趣,文人墨客喜欢养蝈蝈、养蛐蛐,写诗作画,推波助澜,养虫子渐渐成为了一种产业和文化。而一些人竟然对虫子到了痴恋的程度。
王世襄在《京华忆往》中记载,(上世纪)三十年代,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、画家管平湖先生过隆福寺,见到一只蝈蝈,其声雄厚,可惜苍老,肚上有伤痕,腿已残缺,知不出五六日即死去。但是,管先生依然用5元钱买之。当时管先生生活拮据,卖画为生。五元钱能买两袋洋面粉。管先生说:“哪怕活5天,听一天花一块也值。”真是被蝈蝈的鸣声所迷。
王世襄喜欢玩虫子,在上世纪“文革”期间,无书可读,无友可交,无事可做,唯一能解忧的就是蝈蝈的叫声。王先生半夜启程,骑车跋涉,到百里外的山中逮蝈蝈,听蝈蝈鸣啼,慰籍心灵
以前,养蝈蝈、养蛐蛐多是有闲、有钱人所为,那些整日为生计所迫者是无暇为之的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家乡蝈蝈众多,叫声盈耳。大人们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,“鸡刨食似”的整日劳作,是无暇逮蝈蝈、养蝈蝈的。那时逮蝈蝈只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。
八十年代后期,解决了温饱问题,一些人又开始捉虫养虫了。
见成年人逮蝈蝈,是在大学毕业之后。看到他们为了逮蝈蝈,风餐露宿,觉得不可思议。
九十年代始,矿上的闲人很多,夏日里,满街都是打扑克、搓麻将的。
一些退了休的工人就外出逮蝈蝈。他们戴着草帽、带着厚衣,捎着火烧、背着水壶,骑着自行车,一路坑坑洼洼、颠簸几十里,来到山下,翻山越岭,寻寻觅觅,逮蝈蝈。
有一个退休工人逮了数十只蝈蝈,放入两旧暖水瓶壳中,放在窗台。蝈蝈争鸣,一阵一阵,此起彼伏,不仅白天喧嚣,夜里也不停,让人难眠。妻子怒甚,开水浇之,都烫死,真有点暴殄天物。
可此人逮蝈蝈痴心不改,未过几日,家中鸣声依旧。真不知是爱之呼害之呼?
而更多的人是把蝈蝈放进笼子里,挂在窗外。宿舍里有很多蝈蝈声。
前些年,大量使用农药,昆虫难逃厄运,田野里的蝈蝈越来越少,只有那些远离农田的山上还有几只蝈蝈鸣叫。
蝈蝈少了,也越来越值钱了,蝈蝈成了不少人的宠物。在冬天,有人把费尽周折弄来的蝈蝈放在小葫芦里,装在身上的口袋里,走到哪里,蝈蝈就响到哪里,很是神气。
从前养蝈蝈者多是有闲有钱之人,现在,一些贩夫走卒也养蝈蝈了,真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之感。人们的生活变了,蝈蝈的命运也变了。
逮蝈蝈的人也越来越多了,他们为了逮一只蝈蝈,跑出上百里,在一个地方蹲上半天。蝈蝈逮住了,拿在手里,欣喜若狂,到处谝说。
“杯小乾坤大,虫微一季鸣”。蝈蝈虽小,但其鸣声清脆让人喜爱,关乎一些人的悲喜,甚至于虫子的命运,关乎到人的命运。
蟋蟀
秋天的鸣虫,蟋蟀名声最大,原因就是因为蟋蟀好斗。
蟋蟀有很多名字,蛐蛐、促织、油葫芦等。我们老家叫“土蛰子”。
在我国,久有斗蟋蟀的游戏,后来演变成一种赌博。不仅普通百姓斗,公子王孙斗,甚至有的皇帝也斗。
《聊斋志异》中《促织》写道,皇上喜斗蟋蟀,令地方进贡,使百姓家破人亡。人化为蟋蟀,很是悲惨。虽然是怪异故事,但也是现实的反映。
我对斗蟋蟀不喜欢,不过,我还是很喜欢王世襄老先生写的《秋虫六忆》,写的就是逮蟋蟀、买蟋蟀、养蟋蟀、训蟋蟀、斗蟋蟀,十分的有趣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逮蟋蟀,写得活龙活现,妙趣横生,这可能和我自小喜欢逮蚂蚱有关。逮蚂蚱和逮蟋蟀有很多相似之处,只不过逮蚂蚱不需要像逮蟋蟀那样小心翼翼而已。
王世襄老先生潜心研究,还把蟋蟀做成了一门学问。
历史上,蟋蟀是一些文人的宠儿,古代的文人给蟋蟀起了一个很雅的名字“蛩”,于是这不起眼的虫子就入了诗词的天地。“蛩馀窗下月,草湿阶前露。晚景凄我衣,秋风入庭树。”“草际鸣蛩,惊落梧桐”。“蛩 ”在诗词中常常出现,文人们或以蛩声感叹时光变化,或以蛩声表达怨妇思绪。
不过,无论文人描写的怎么美好,我却不怎么喜欢蟋蟀。儿时的乡间,一到秋季,遍地蛩声。尤其是到了夜间,不止窗外蛩声不断,有时屋内也有蛐蛐的鸣叫声,“蛩声绕罗帏”,忧人清梦。更可气的是蛐蛐经常夜间到锅中,早晨掀开锅盖,几只蛐蛐拼命跳出。若是锅内有食物,也被它们弄脏了。因而,家人对进入屋内的蛐蛐是杀无赦。那时,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蛐蛐。
后来,我发现,有些地方比我老家的蛐蛐多得多。一九八七年,在山东平邑石膏矿实习。石膏矿处野外,远离村庄,周围都是农田。石膏矿内几座平房,显得荒凉。到了夜晚,屋外有几盏很明亮的灯。灯下几平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蛐蛐,或静或爬,或飞或蹦,让人咋舌。几个妇人拿着塑料袋逮蛐蛐,很快就逮一袋子。
毕业后到了泰安肥城,肥城紧邻宁阳,也是历史上盛产蛐蛐之地。王世襄在《秋虫六记》中写道,肥城、宁阳的蛐蛐不少被运到京城卖。
到了秋后,地里的玉米秸底下,有不少的蛐蛐,长大肥硕。
妻子是肥城人,说蛐蛐能吃,和蚂蚱差不多。我尽管喜食蚂蚱、知了、豆虫等,可不想吃蛐蛐,觉得不干净。在妻子的诱惑劝说下,我们逮了一些肥大的蟋蟀。处理干净了,用油炸了,味道还可以,不过有股玉米秸味。
现在,却很少听到秋虫的鸣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