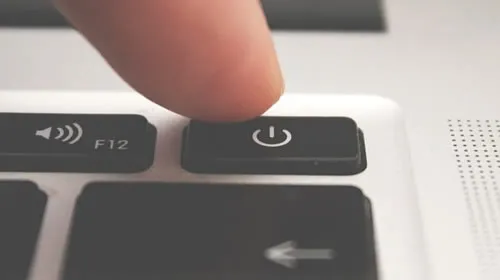作者:乔故
1
盛一一十七岁那一年,香港下了一场大雨。她躲在便利店的檐下,雨水从她的鞋底灌进,再从脚后跟溢出。
大雨里,黑色的豪车缓缓地停下来。司机对着坐在后座的男人,指了指便利店外蹲着的小女孩,说:“先生,你看。”
突然,一把黑色的大伞挡在她头顶上,盛一一抬起头,愣愣地看。她的马尾被雨打湿,看起来有些杂乱,还有少数头发黏在她的脸颊上,她没有刘海儿,一双眼睛格外动人。
撑伞的是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,二十四五岁的模样,伞外就是雨帘,他和她说话,似乎把一切雨声都隔绝在外:“叫什么名字?”
他的声音低沉,带着成年男性的磁性声线。一句纯正的粤语从他口里说出来,分外动听。
她来香港的时间不算短,仍旧只能大概听懂却不会说,她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,歪头看他,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:“一一,盛一一。”
盛一一看着他的手指,他中指处有茧,是常年握笔的缘故。
他勾起薄薄的唇,朝盛一一伸出一只手:“我带你走?”
她抿了抿唇,点点头:“好呀。”额头上的水珠顺着她脸的弧度滑落到下巴。她小心地把手放在他手上,他的手掌很大,掌心干燥温暖,平白使人安心。
2
网上关于盛一一的黑料简直可以再扒三天三夜。炒作、耍大牌……
盛一一在窝单人沙发里看着这个月的娱乐报刊,上面醒目的位置写着加黑的一行字——流量小生林青又深夜同S姓女星回家,疑似同居,动作略显亲昵。
北城的春季多雨,刚入春的天有些微凉,盛一一瑟缩了一下,助理就懂事地把披肩和热茶递到了她面前。她接过望向窗外,雨突然大了些,拍打着窗户。
小助理对着她说:“一一姐,陆总让您待会儿回公司一趟,有事。”
依照娱乐圈的标准来算,盛一一算不得高,又因为长年吃着减肥餐,整个人瘦瘦小小的,额头上缠了绷带,是前些日子拍戏不小心受的伤。她窝在沙发里,缩成小小的一团,亚麻色蜷曲的长发挡住她的神色,看不太清晰。
小助理远远地看着她,似乎觉得这样的盛一一有些……难过落寞。但小助理随即又摇了摇头,她有什么好难过的呢,年纪轻轻就斩获大奖,又因为陆总的关系在娱乐圈顺风顺水,大概这一生也没有遭受过什么磨难。
盛一一敲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,陆朝越正低头签文件,他轮廓凌厉,眉目冷淡。
桌子上是一份娱乐报刊,标题下配了一张图片,虽然模糊,但仍旧看得出是林青又搂着她肩膀的照片。
盛一一一下子说不出话来,喉咙像是被人扼住,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:“陆总。”
陆朝越抬起头来,把文件搁置在一旁。他的手指修长,骨节分明,一下一下地敲在桌子上,手指旁就是那份报刊。
“上次是名导严瑞,这次是林青又,那下次呢?”他嗓音低沉,似乎是商量的语气,“这样,一一,你告诉我,下次是什么事情,我好让公关部那边提前给你写好通稿,不至于像现在一样,被打得措手不及。”
盛一一没说话,自顾自地坐到了他对面的椅子上。室内暖气明明开得很足,盛一一却觉得有些冷,从心窝子里泛起一股凉意,她紧了紧身上的披肩,说:“严导的事我上次已经解释了,至于报纸上这个,是因为庆功宴太晚了,林青又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回家,所以送我回去。”
陆朝越合上钢笔笔帽,语气有些严厉:“盛一一,你知道自己身上挂了多少个代言吗?是嫌网上的爆料还不够吗?你究竟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?”
任性?他的字句有些重,落进盛一一的耳朵里,震得她心脏都狠狠地痛起来。
她的思绪越飘越远,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吧。她那个时候十七岁,陆朝越把无家可归的她带回了家。她刚去陆朝越家里时,还没有进娱乐圈,一张脸未施粉黛,眼神干净澄澈。
她个子小,别墅里的用人丝毫不把她放在眼里,只当是自家先生捡随意回来的孤女。那个叫“琳达”的女佣,似乎很瞧不起她,盛一一听到她对别人说:“那个叫盛一一的,我看她比‘那位’的段数还高几级呢,小小年纪就这么会耍手段,长大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。”语气里是藏不住的鄙夷。
盛一一从旋转楼梯下来,和琳达闲聊的女佣戳了戳她,示意她盛一一就在后面。可琳达转过身瞥了她一眼,话说得更加难听。
突然一杯水泼下,琳达精心做的头发被打湿,她像只奓毛的猫一样跳起来,涂着鲜红色指甲的手指着盛一一:“你敢这么对我?!”
盛一一站在楼梯上,理了理衣角,嘴角扯起弧度,漫不经心地道:“嗯,算是我给琳达小姐背后总念叨我的回礼。”
陆朝越知道了这件事后,辞退了琳达。
盛一一有些惶惶不安,晚上陆朝越来指导她写作的时候,她咬着笔帽,抬起巴掌大的脸蛋看着他,模样惹人怜爱又小心翼翼:“我今天是不是很任性?”
陆朝越勾起薄薄的唇,眼底笑意盈盈:“怎么说?”
她像是认真地反省:“因为明明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的。我大可以当作没听到,或者和她好好谈一谈,再不济也该告诉你,让你来解决,不应该这么冲动。”
陆朝越在稿纸上标注了用错的字词,又把正确的写在一旁,头也没抬:“你检讨得这么认真,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,你还会用冷水泼她吗?”
盛一一把改好的文章拿过来看,她看的时候,背挺得笔直:“知道了。”她顿了顿,“应该用热水才对……”
陆朝越笑了笑,手掌落到她头上,揉揉她的脑袋,语气宠溺,“不任性,我们一一就算把天捅出个窟窿,我也能给你兜着。”
3
盛一一低着头,手里把玩着她的长发。
你瞧,人就是这样,说过的话,做出的承诺,都可以随意忘记。这个人曾告诉她,她可以任性,她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,这个人曾把世间好的东西都捧到她面前,曾把她捧到云端之上。可如今,这个人又说,我给你的那些东西我都要收回来,你配不上。
盛一一嗤笑一声,窗外的雨渐渐变小,室内安静地只听得到她和陆朝越浅浅的呼吸声,大概是办公室太空荡的缘故,她的声音显得有些缥缈:“陆总,我不想做这一行了。”
陆朝越愣了愣,为她的称呼。
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?她不叫他“陆哥”了,要直呼他的姓名。他父母离异,自小跟着爷爷长大,受了老一辈的思想的感染,一向比较在意辈分这种事情。盛一一第一次喊他名字的时候,他皱着眉:“盛一一,你怎么说话的呢?”
哦,好像是她十八岁那一年,她坐在小阳台的藤椅上,抱着书看,目光从书上挪下来,些微的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洒进她的眼睛里:“陆朝越,我就这样说话的呢。”
陆朝越凑近了她一点儿,曲起手指敲在她头上,力气使得有些大:“没大没小的。”盛一一捂着脑袋,疼得五官都皱在一起。
她缩在藤椅里,穿着坦领的荷绿色衬衫,露出好看的锁骨,刚洗过的头发带着清香。
陆朝越的喉结滚了滚,头一次发觉,原来那个从前躲在香港便利店下的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。
他思衬着,虽然小姑娘的脾气跟着年纪一起长,但总归算是自己带回来的姑娘,除了宠着还能有什么办法?
反正不过一个口头称呼而已,她乐意怎么叫,就怎么着叫吧,陆朝越想。
陆朝越抬起手捏了捏眉心,点燃了一支烟,看着面前的盛一一:“行吧,这些年为了你,不管是公司还是我,都是挺累的。”
烟草的味道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,盛一一皱了皱鼻子,站起身来,准备离开。陆朝越喊了她一声:“我这里有把伞,你拿着走吧。’”陆朝越看了一眼她微微湿润的长发,“多大的人了,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她怔了怔,摇摇头,步子没停,说:“不用了,我带了伞。”
他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说过话了。
那是一个平常的雨夜,陆朝越公司出了点儿事,在书房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,只喝了咖啡垫肚子。
指针指向一点的时候,他终归放心不下,推开门想去看她睡了没有,却见她抱着膝盖在床上小声啜泣着。
陆朝越走过去抱着她,哄小孩子的语气:“怎么了,别哭。”
他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烟草味,盛一一哭得通红的眼睛看着他:“我做了噩梦,梦到以前……”
陆朝越没想过盛一一会对他敞开心扉,她依赖他、信任他,可从未说过她以前的事。他知道,他的一一,一直都是一个坚强的小姑娘。
可此时此刻,他所以为坚强的小姑娘,手指紧紧地攥着他的衣襟,语气里含着浓重的颤音:“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和你说过我的父母?”
她其实已经记不太清从前的事情了,关于爸爸妈妈,她也只记得幽暗潮湿的小房子里,常年充斥着烟酒的气味,父亲的谩骂声和母亲的哭啼声。
父母死于意外,两个蝼蚁一样的人而已,死了就死了,有谁会在意的?
她原以为自己会被饿死,可她遇到了陆朝越。
他看起来那么耀眼,那么温暖,就这样强势的挤进她的一寸天地。
他说要带她走,但那终归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盛一一出门的时候,没忍住,到底还是回头说了句:“我听说,你和顾如沐好事将近了?”
4
盛一一刚出道那几年,常有媒体拿她和顾如沐做比较,称她为“小如沐”——她一双眉目生得和顾如沐有五分相似。但顾如沐长她九岁,年纪轻轻就拿了影后,圈内都夸她敬业、努力、为人谦逊。
但现在人们谈到顾如沐时,都会遗憾惋惜地说上一句:“如果不是当年的事情,现在哪里还有盛一一的位置?”
圈子里对盛一一的评价不太好,据说她曾经在大导演的饭局上,对那导演怒目而视,掀桌而走。
陆朝越花了好多心力才替她摆平,她葱白的手指翻了一页剧本,语气淡淡:“那个导演不正经,我没有打他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”
陆朝越叹了口气,戳了戳她的额头,语气宠溺:“总是这么任性,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一行,怎么劝都不听?”
为什么?盛一一陷入沉思,陆朝越以为她要说什么追求梦想之类的场面话,她却一本正经地开口:“还不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,就这样默默无闻不拿出来分享显得有点儿自私?”
他失笑,又伸出手摸摸她的脑袋。
她拿了大奖,在镜头前,红唇启启合合:“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不要再称我为‘小如沐’了,我盛一一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。”
有记者提问,问题刁钻:“盛小姐觉得自己是实至名归吗?”顿了顿,语气刻薄,“我的意思是,不依靠陆先生的话。”
她拿着话筒毫无难色:“是啊,我觉得自己实至名归呢。”她也学着记者的模样,顿了顿,“我是说,不依靠陆先生。”那模样,实在张狂至极。
点击下方“继续阅读”看后续精彩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