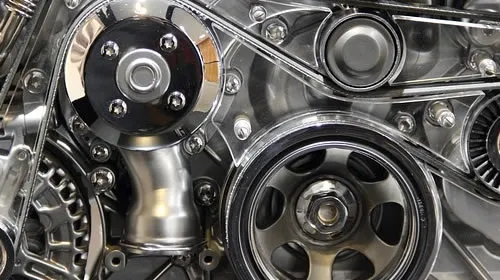刘宜庆(柳已青)
元宵节又叫花灯节,上元节。看,天空圆圆的月亮,多像一枚汤圆。
2路公交车拖着长长的辫子,发出“嗡嗡嗡”的声音,行驶在天津路上。
寒风刮起雪地上红色的鞭炮碎屑,在行人的脚脖子处回旋。即使平常热闹非凡的中山路,此时也静悄悄的,空旷中,带着一点冷清。偶尔传来一声鞭炮的响声,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燃放的。大年十四的下午,天已接近黄昏。但是,天津路2路车站站牌下排着长长的队伍,向着一个窗口缓缓移动。
原来人们在寒风中,忍着寂寥和寒冷,排队等待买元宵。长长的队伍中,人们踮着脚尖,看着自己前面的队伍越来越小,而往后看看,队伍越来越长。终于轮到自己了,急急地把早就准备好的钱,递进窗口,连声说:“一盒花生馅的,一盒芝麻馅的,一盒草莓馅的。”
正月十五的两种色彩:花灯红,元宵白。
元宵,又叫汤圆,正月十五的应节食品,各大超市,都有的卖。为何单单钟情这家的元宵?“水磨糯粉、石磨造馅,手工包制、现做现卖。”青岛人都认大老李汤圆。说起来,卖大老李汤圆的地儿,真简陋,只开了一个窗口,没有店面供顾客进店选购。即使这样,也阻挡不了长长的队伍,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几天,排老长的队买大老李汤圆,成为天津路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致。
2004年的春节过后,那时半岛都市报还在潍县路55号。正月十四那天下班后,天空彤云密布,夜色已经降临,我走到天津路上,排在长长队伍的末尾,等着买元宵。那时,手机还没有上网的功能,不能刷微博玩微信消磨无聊的时光。只好调动大脑里关于元宵的信息,想啊想啊想。
元宵节吃元宵,天上一轮圆月,人间阖家团圆。打开锅盖,热气散开,将白白嫩嫩的元宵舀入圆圆的碗中,浮圆子在汤中,宛如天上的圆月。这种食品最早出现在宋代,当时人们将之称为“市中珍品”。宋人周必大写过一首《元宵煮浮圆子》诗:
这种糯米球煮在锅里载浮载沉,所以宋代叫“浮子”。正月十五是上元灯节,是宋代文人词人的情人节,也是官民同乐的狂欢节。宋代的大都会,市民观灯深夜始散,煮浮圆子作为宵夜,吃出了甜蜜、幸福和安康的感觉。灯象征了光明与温暖,元宵代表了团圆与甜蜜,成为上元节永恒的符号了。
今年的元宵节,由于疫情,家庭团圆,观灯就略过。
随着前面的队伍渐渐缩小,忽然想起,元宵为何又叫汤圆,这里面有一段历史掌故。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,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,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和袁克定等人,授意制造了民意舆情,劝进登基。但袁世凯仍然有些顾虑,人在这个关头,变得格外敏感和多虑,同时也格外迷信。1915年年底,袁世凯宣布:1916年改为“洪宪”元年,实现了他的皇帝梦。转眼间到了1916年的元宵节,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卖元宵的吆喝声。此时,袁世凯遭到举国反对。元宵,元宵,不就是“袁消”“袁消”吗。袁世凯听了,心惊肉跳。这种不吉利的兆头,让他坐卧不安。于是,下令改名为“汤圆”。
从那以后,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:“大总统,洪宪年,正月十五夜难眠。全国‘元宵’改‘汤圆’,‘汤圆’改了改‘汤团’。明年‘袁消’后,谁还叫‘汤团’?”到了后来,有人写打油诗讽刺此事:“诗吟‘圆子’溯前朝,蒸化煮时水上漂。洪宪当年传禁令,沿街不许喊‘元宵’。”
有一碗热元宵,有家人陪伴,庚子数年的元宵节,就是圆满。
“绝怜高处多风雨,莫到琼楼最高层。”小小一粒汤圆,绊倒了一代枭雄袁世凯。这汤圆,不仅情系人世的悲欢离合,还牵动历史的跌宕起伏。元宵多了一段掌故。这掌故可以拿来下酒。
就这样想着元宵的故事,前面只剩下两个人了。当我买上大老李汤圆,感觉脖颈中有一羽清凉,抬头看,天空飘起了雪花。大片大片的雪花,好似洁白的鹅绒,从高远的天空,降落。有风,但不大。雪花御风,仿佛轻盈的舞蹈,在昏黄的灯光下,悠悠而下。
我提着三盒大老李汤圆,走向小港,去乘303路公交车,回李村的家。后海的风大,寒意逼人。雪花依然优雅,没有失去自己的节奏,只不过越下越大,越下越密。等车几分钟,雪花温柔地覆盖了大地,变成白色。拎着汤圆,用手指摸一摸,汤圆处于冰冻的状态,指尖微凉。心中却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——笃定与安宁——一点也不觉得冷。
多年过去了,难忘元宵给我的这种感觉。
2013年春节,翻看闲书,偶然看到宋代诗人姜白石的“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唤卖汤圆”之句,以传神之笔,描绘轿中客人钩帘看街时的情景,和不吃到汤圆不肯回去的心情。在那一刻,时光倒流,雪夜排队买元宵的种种细节,如在眼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