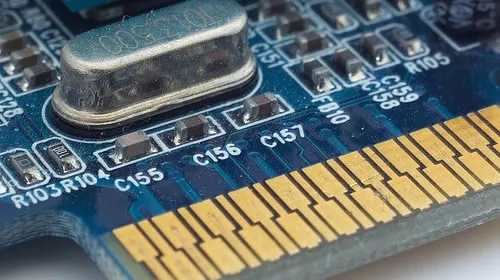捣江湖可能各地都有自己的解,但我们镇江这一带解释可能就是忽悠的意思吧,也就是不做实事的那一种。
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说吧。我有一个同学以前跑供销也跑得不错,发了点小财,之后呢就有点小富即安的感觉了,出差也少了,在村里找人打打麻将玩玩,几年之后一点积累也用光。这时他就开始捣江湖了,一会儿到这个同学面前说有什么业务要用点钱,一会儿到那个同学面前说有业务要用钱,同学们一开始都以为他干得还不错,所以开始他都能借到钱,但时间长了马脚就暴露了,再也没有同学听他捣江湖了。
上海人的“捣浆糊”
在方言的江湖里,有些词是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单纯理解的,得从语气语调里去理解,正如俗话讲“听话听声,锣鼓听音”一样。上海话里的“捣浆糊”一词即是一例。

捣浆糊这个词语,经过上海人在世俗的语言环境中不断打磨,其内涵不断丰富,功能不断得到强化,在不同的声调加持下,它能表达的意思多种多样,通用性也越来越强,犹如葱姜在荤菜料理的角色一样,放进去大错不错。
过去,浆糊在市民百姓生活里露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记得小时候看到家庭主妇们自己扎鞋底,粘布鞋底就要用到浆糊。还有,家里自己做衣裳,衣服里的“硬衬”,即服装里的衬料就是离不开浆糊的。
以前家用的浆糊都是靠自己调制的,因为用量不多,一般不会用后来的所谓化学浆糊。浆糊的用料一般是食用的黑面粉,即标准粉。在煤球炉上放一只旧的钢精镬子,镬子里是用水稀释过的面粉,一把长勺子不停地在镬子里捣,镬子越热,捣的速度越要快。浆糊捣得好,就要做到上面不起泡,中间不起块,下面不粘底,这样的浆糊均匀稠密粘性好。不少家庭的捣浆糊都由小朋友做,因为好玩,小朋友也乐于做,但是常常玩过头了,明明浆糊已经捣好了,玩劲还在,继续捣,结果火候过了,浆糊粘底了,就再捣捣伊,浆糊结块了,再捣捣伊,浆糊烧焦了,为了掩盖掉焦糊味,不被家里大人发现,加点水再捣捣伊。可见捣浆糊的关键就是一个“捣”字。
我以前很不喜欢捣浆糊这个词,因为觉得那就是不正经做事,或者遇事推卸责任,模糊是非的“瞎胡调”。后来发现在上海人的语境里,这个捣浆糊的含义在不断延伸变化,在原本贬义的外貌下,竟然捣出褒义的内涵来了。比如把能协调事情称作浆糊捣得好,善于协调事务的人自然就是捣浆糊的能人。又如把善于打圆场,消除社交场合的尴尬气氛,也称作会捣浆糊,把善于平息纠纷、兼顾各方利益撸撸平的“老娘舅”称作捣浆糊高手等。如此这般下来,捣浆糊这个词就升级为兼具褒义和贬义的全能词了。但要听懂其所表达的真义,得听语调,甚至还要看说话时的面部表情。犹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调侃话,“女足谁也踢不过,男足谁也踢不过”一样,句子一样,语调的细微变化,意思就截然不同;而要分辨清楚上海人口中出来的“捣浆糊”是什么意思,不谙上海的世俗文化环境,即使感觉到语气语调的变化,也未必能分辨出内在的含义。
不过细想起来,上海人口中的捣浆糊,是有原则的,即使是特别会做人的所谓“老浆糊”,如果没有原则的“瞎胡调”也会被人看不起,也不会有真心朋友。
没有原则,没有是非观念,不正经做事的人,上海人称其为“浆糊桶”。
其实,从上海人捣浆糊这个词的广泛使用,也可隐约感受到上海人求太平的为人处世的习性,随方就圆,顺水推舟,凡事不冒尖,遇事抹抹平,给人留面子,看穿不讲穿,王顾左右而言他,是非之地不置可否,这里面有几分智慧,几分善意,甚或几分狡黠。在很多上海人看来,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,有中间地带,有时候多一点冗余度挺好。(羊郎)